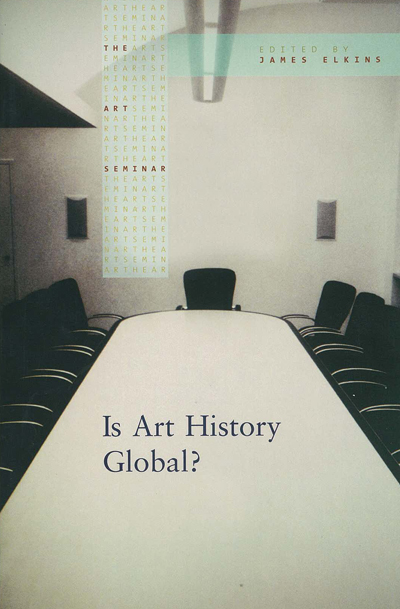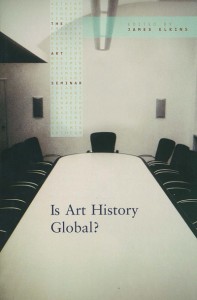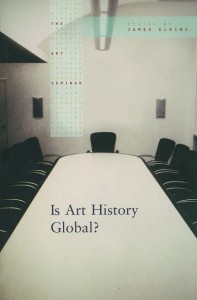:: 总介 ::

柯律格(Craig Clunas),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美术史,尤其是明清物质文化。柯律格曾于1974年前往北京学习中文,分别于剑桥大学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取得学士与博士学位。柯律格曾担任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中国部资深研究员兼策展人十余年,并先后任教于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和牛津大学。他于2014年担任大英博物馆(Britism Museum)年度展览”明朝:改变中国的五十年”的策展人。
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美术史论与批评系主任。
《艺术史是全球的吗?》是一本讨论艺术史理论走向与方法论的文集,其中收录了不少当今研究西方及非西方艺术史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史家们。文集包括埃尔金斯作的序,拉美艺术史学者Andrea Giunta, 德国艺术史家Friedrich Teja Bach, 捷克艺术史家Ladislav Kesner等几位学者的论文,于2005年举办的“艺术研讨会”(The Art Seminar)实录,及众多未能参会的艺术史家的书面回应。这些回应中就包括柯律格。
在序言中(19-20页),埃尔金斯指出了当下“艺术史要依靠西方的理论模式展开”的问题。除西方理论之外,艺术史上并没有一个在理论和概念上独立的国家或地区传统。就中国艺术史来说,他指出,中国艺术史研究需要的原材料和概念非常不同,但是其阐述方式却依然很“西方”。中国艺术史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学,研究中国艺术用的都是同一套理论体系——心理分析学,符号学,图像研究,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等。他们构架和支持论点的方式也和西方艺术史家一样:论文摘要,档案证据,前人文献综述,带脚注的讨论。经典艺术史教材如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的书也被翻译到中国,并在北京,杭州,南京等地教学使用,被一概应用到分析西方和非西方艺术中去。难道中国不应该使用自己原生的术语和理论来阐释中国艺术吗?现实中的答案是并没有。
因此,埃尔金斯大胆提出,并不存在“非西方”的艺术史。
那么,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61页),埃尔金斯给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例子。他指出,巫鸿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用了一些中国的艺术分类模式和概念,但是阐述路径依然是西方的。其他稍微没那么出名的学者倒是有一些系统性抵制西方阐述的尝试。比如,曹意强,他采用了9世纪中国唐代艺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的元素;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他提出西方史学家借鉴司马迁的平行叙事结构;佐藤将之(Masayuki Sato),他建议重新研读8世纪中国唐代的刘知几的《史通》。
值得注意地是,在《艺术史是全球的吗?》一书中,当众多学者讨论“非西方”艺术(主要指亚非拉地区的艺术,也包括捷克这样的前苏联国家艺术)时,经典西方艺术史教材和相关艺术理论依旧是讨论的基本共识,中国虽然是时常被拿来引用的例子,来自东亚地区的作者也仅有一位日本学者稻贺繁美(Shigemi Inaga)。这场讨论依然是在英美国家举办的、用英语进行的讨论,依然把“西方-非西方”这种二分法视为天经地义。
本文翻译的是柯律格的回应节选。
:: 译文 ::
《工具箱与教科书》(节选)
在这场丰富的交流中,有如此多的材料,以至于连“审视”的想法都变得多余。而所谓全球视野的引入——大写的艺术史——让这一切都变得更令人望而却步。我只能从我目前工作领域的具体角度来回应。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艺术与考古系有点像传统的占据英国主导的那种欧洲中心(Eurocentric)的院系,仅仅是翻转了镜子的另一面来看。
我们只“做”亚洲和非洲。像乔托(Giotto)到塞尚(Paul Cézanne)这一串名字是我们本科基础课中不提的。因此,可以说,我们是个试验床,试验是否一套不同的内容就一定等于一套不同的艺术史。我必须不客气地说,从我们现有的情况来看,基本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们课程大纲上的名字可能不为人所熟悉,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令人不熟悉的了。奥黛丽•罗德(Audre Lorde)(美国加勒比裔女性主义激进作家——译者注)的名言就足够容易令我们中枪了,“主人的工具是绝对不可能拆掉主人的房子的。”然而,同样也可以说,如果忽略了主人是拥有一套拿来造房子的工具箱的这个事实,那么就基本没可能拆解任何事情了,如果最终目的是为了拆的话。这么说是因为,对我们学生来说(在本科和硕士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都是有亚洲和非洲背景的),一些关于“工具箱”(意即西方理论——译者注)的知识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我要断言,当学生们因为觉得没必要而迅速略过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和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理论书(以及一些最新出版物),并拿起诸如《中国艺术的风格》《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的一些社会和经济背景》《美的历程》之类的书时,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评价这类书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做,怎么做,甚至也没法真正做到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做“艺术史,正如埃尔金斯所说的那样,不可避免地成为做西方艺术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说“中国艺术史”是“西方的”,那我觉得这就好比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东方的”一样搞笑——因为火药是他们作战的中心环节。
我在这场对话中感到了一些不安,一种存在于“西方及其它区域”这种吸引人的范式,和一个更微妙的(至少从影响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关于全球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未来可能是什么的把握之间的不安。对我来说,关于这种微妙最好的表达在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2000版)一书中。这本书很简明扼要地描绘出亚洲精英对于构建出“欧洲作为现代性”这样的假设的复杂情结。
举例说,正如现在已经被广泛研究的,日本词语“美術”(bijutsu)是如何作为对19世纪德语schöne Kunst(意即“精美的艺术”,英文翻译为Fine Art——译者注)的仿造词出现的,这个词又是如何传到中国、以同样的汉字成为“美术”一词的。如今,任何一本字典都会告诉你“美术”的意思就是“艺术”。因此,你可以说,在中文语境中讨论的美术史其实是日语(这种说法非常冒犯中国的爱国情操)。但是我们倾向于不这么说,因为我们更着迷的是东西方的相互影响,而对于1850-1950年这一个世纪的术语演变不那么感冒——这也正是我们所谓的艺术史的形成期。姜苦乐(John Clark)的作品,或者年轻学者如阮圆(Aida Yuen Wong)的作品,正在试图还原这一时期部分复杂的中日交流,虽然影响微弱但最终还是传到了欧洲和北美,成为今天英语学界讨论中国艺术界的部分。
(关于所谓的完美艺术史教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北美的问题。英国一向不鼓励用一部大卷本做教材,也几乎没有一个英国的艺术史系只用一本系统的教材,“詹森”或者“昂纳和弗莱明”的经典教材在英国影响很小。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我觉得这源于一种对牛津剑桥式的精英教育的怀旧,源于一种理想化的情绪,其中只有一小撮学生可以享受的“开卷有益”。于是在当下就转化成一种对于单一大卷本教材的不信任。
…
我们从来不能小看大众对于艺术的慰藉心灵力量的向往,以及大众文化中关于艺术的讨论。同贡布里希(E. H. Gombrich)于二战后写的《艺术的故事》(Story of Art)一样,李泽厚于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几乎同样畅销。这本书安慰了一代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让他们明白,尽管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高雅艺术还是幸存了,并且是有价值的,以及他们认为自己(于文革前)所知道的关于艺术和美的一切还都是对的。
就在2005年9月,BBC晨间新闻作了一项广泛的调查来寻找“英国最伟大的绘画”——超过10万人从一份并不出彩的十位候补名单中在线投。赢家是特纳(J.M.W. Turner)的作品《战舰,她最后的泊与击》(“The Fighting Temeraire Tugged to Her Last Berth to be Broken Up”)(1838年)。
J.M.W. Turner, “The Fighting Temeraire Tugged to Her Last Berth to be Broken Up”, 1838,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UK.
这是否就是Kesner(Ladislav Kesner,捷克艺术史家——译者注)所谓的”艺术的庸常化”?还是说,这意味着,由于艺术史对于艺术评论的摈弃,艺术史本身变得边缘化,而艺术评论却蒸蒸日上?必须注意地是,当许多正值创作期的艺术家被邀请提交评选候补名单时,却没有一个艺术史家受邀这么做。
今天,BBC和艺术以及艺术史的关系,已经不比当年了。35年前,我还是个学童,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还在讲《文明》(Civilization),告诉我什么是,什么不是。我的观点不会被引用,也不会有人投票。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同样甚至更为着迷的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艺术的BBC系列——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1972年)。我认为伯格直接挑战了埃尔金斯关于克拉克文明史的权威无人能敌的论断。这套节目直到今天还在被讨论,这本书还在出版,还留在无数大学的书单上。当我16岁时,穿着俗气的衬衫和喇叭裤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格,和穿着庄重花呢的的克拉克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对比。伯格猛烈抨击的事物包括宏大叙事,关于艺术天才的迷思,艺术品不过是一种商品,男性的凝视,等等。
约翰•伯格与与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分别在BBC电视节目
然而,三十多年后,《战舰》依然能够成为“英国最伟大的绘画”(当然,我不是说这不是一幅伟大的画)。这对艺术史家的自尊来说不知是何滋味。想象一下,与这一连串令人舒心的伟大作品相比,一些更丰富更复杂的作品,却从来没有被更广泛的公众所认识。这也许是个痛苦的事实,但至少这幅画还有机会被认识,被评估,然后被遗忘。
…
我也许从英国本土经验出发说的太多了。…不过,在今日,跑去中国大书店的艺术专架看一下,你就会发现文化和经济资本的相互影响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极度活跃着。有迹象表明,一种新的关于艺术“价值”的、把审美和市场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写作流派在出现。这点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和米勒的《古董定价指南》(Miller’s Antiques Price Guide)很不一样。
如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关于中国艺术的最多作品出现在中国,并且用中文书写——尽管是一种充满了新的仿造词的中文。一大批原本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艺术的书正在被翻译成中文,通常是经由目前活跃的中年学者之手。很快你就不需要英语来读这些作品了。我相信,不出几年,在中国就会出现一个不需要英文也可以自如运转的艺术史圈子。这种变化是惊人的。反之,在英国,语言能力的下降是灾难性的,这给艺术史带来了真正的危机,因为这意味着研究只能在英文文献资料中进行。这比艺术史学科中是否存在原创性的概念更令人悲观地多。
:: 原文出处 ::
柯律格,“工具箱与教科书”,节选自詹姆斯•埃尔金斯(编)《艺术史是全球的吗?》(2007年纽约Routledge版)279-285页。
Clunas, Craig, “The Toolkit and the Textbook”, in James Elkins (eds.), Is Art History Global? , New York: Routledgge, 2007, pp 279-285.
::译者简介::
刘菂(b.1989),中英文自由撰稿人,曾在中国、香港、英国、瑞典、美国等地学习和工作,现居伦敦。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主修社会学、法律与艺术史,现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合办的设计史硕士专业在读。